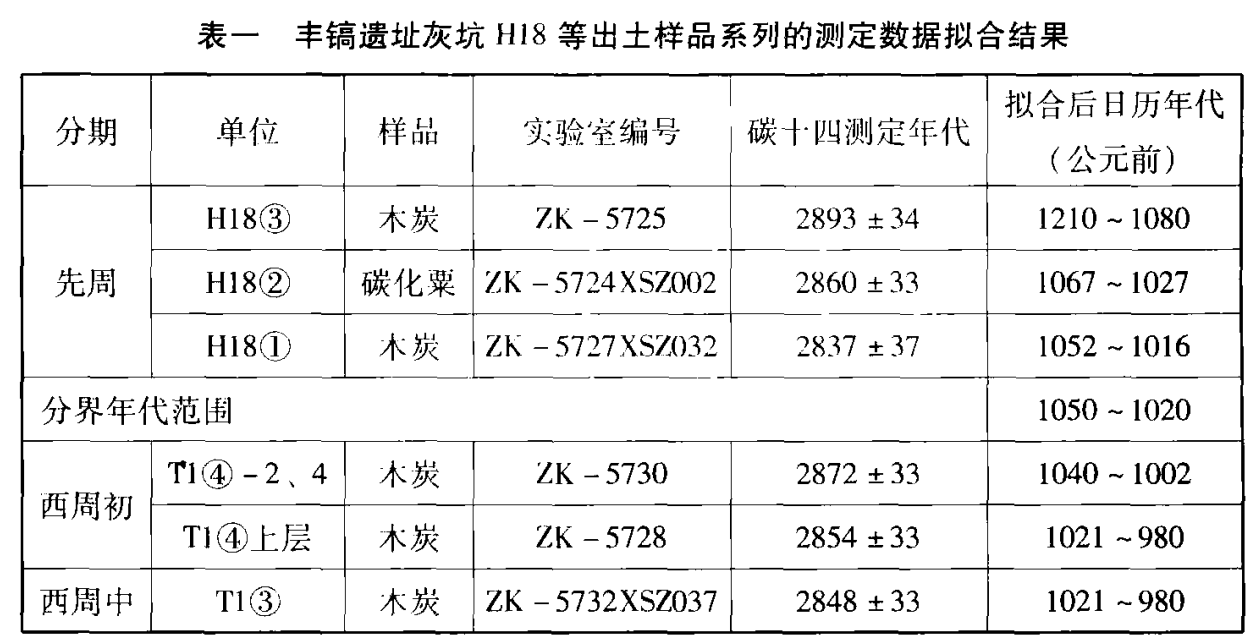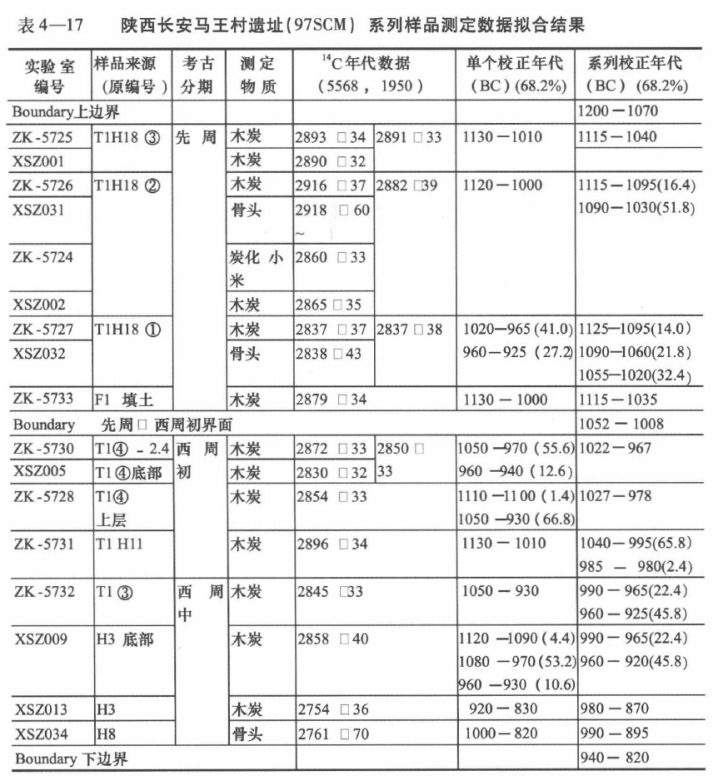夏商周断代工程可信度有多高?
96 个回答
1.年表不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全部学术结果,如何评价夏商周断代工程不等于如何评价年表。
2.考古学不是历史学(特别是在史前考古和原史考古范围内),考古学长于把握大的时空坐标下的文化变迁,对微观的历史事实不可能完全掌握,此所谓考古学的局限性。即使是使用高精度测年和天文学方法,在缺乏能将三者相连的可信文献记载的情况下得出的任何数据都不可能是精确的,而文献记载(《古本竹书纪年》、利簋铭文)往往是孤例,所以没有办法证明记载可信,很难得出准确纪年。
3.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个卓越的学术贡献是进一步推动了自然科学与考古学及其他科学综合结合的研究方法,使考古学与其他科学的关系更加紧密。而这种方法已成为后世文化工程和考古学研究的主流。
4.夏商周断代工程硬伤处处,如
@花毛提到的武王克商年代问题,另外还有报告编写问题和学术道德问题(参李维明:《郑州青铜文化研究》),从考古学的角度讲,报告编写问题是最严重的。
5.一时脑热的学术攻关难以达成令人信服的成果,但不代表这种攻关没有意义且没有成果。比如断代工程结束以后,文化工程执行者充分意识到年代学特别是绝对年代的把握是较为困难的,并且转入以聚落考古为中心的文化动态过程研究中(不知能否标志文化历史研究的破产),而这一转向影响了考古学之后近10年的发展方向。
6.总体来说,断代工程的主要学术目的(提供年代或年代框架)虽有所突破但并未取得实质性的成功,但在其研究过程中暴露的问题和取得的收获一直在给中国考古学输送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