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的免疫逃逸能力到底是什么
从22年12月全国逐渐放开以来,以石家庄、北京开始各地陆续迎来感染高峰。北京、上海相继发现BA.5变异株,BA.5亚型传播能力更强,具有更强的免疫逃逸能力。也正次这次放开后,很多人出现的疑问的原因:为什么管控的时候没有这么大面积的感染?为什么一放开就这么严重?放开后的感染也并非是“无症状”,几乎90%的感染者都是有症状,那么到底还会有几次感染?为什么会复阳?为什么“专家”说了3个月内不会复阳,结果很多人一两个礼拜就又开始发烧?
不谈正侧,只讨论二次感染的原因——病毒的免疫逃逸。
本文一共2223字,阅读大概需要10分钟。
1、什么是病毒的“免疫逃逸”
2、病毒为什么会变异?
3、新冠病毒为什么会导致重复感染?
————————————————
第一部分:什么是“免疫逃逸”
免疫逃逸是免疫抑制病原体通过其结构和非结构产物,拮抗、阻断和抑制机体的免疫应答。
病原体的免疫逃逸机制:
1.抗原性的变化病原体的中和抗原,可经常地持续性地发生突变,逃逸已建立的抗感染 免疫抗体 的中和和阻断作用,导致感染的存在。
2. 持续性感染 胞内病原体可隐匿于胞内呈休眠状态,逃避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攻击,长期存活,形成持续性感染。
3.免疫抑制病原体通过其结构和非结构产物,拮抗、阻断和抑制机体的免疫应答。
——以上是百度百科对于“免疫逃逸”的解答
免疫逃逸,指的是病原体或者肿瘤细胞,通过不同的机制,逃避集体的免疫识别和攻击。对病毒等病原体来说,形成免疫逃逸的机制包括:抗原变异、前夫必读和干扰免疫系统等。其中,抗原变异是包括新冠病毒在哪的RNA病毒较为常见的免疫逃逸方式。
而对于部分病毒而言,人体在感染后或者接种疫苗后较长一段时间内,不会再感染相同的病毒。
————————————————-
第二部分:病毒会变异几次?为什么新冠病毒会导致短时间复阳?
首先来看一片2021年发表在国家地理杂志上的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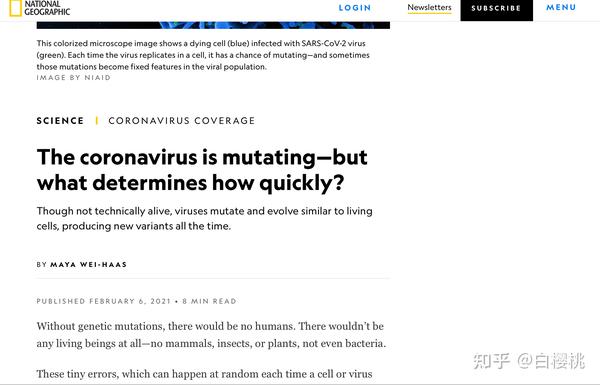
没有基因突变,就不会有人类。也根本不会有任何生物——没有哺乳动物、昆虫或植物,甚至没有细菌。
每次细胞或病毒复制时,这些微小的错误可能会随机发生,为进化提供了原材料。突变会造成种群的变化,这允许自然选择放大帮助生物茁壮成长的特征——伸展长颈鹿的长脖子以达到高大的叶子,或伪装毛毛虫如粪便来逃避鸟类的注意。
然而,在大流行期间,“突变”一词引起了更不祥的注意。病毒虽然在技术上并不活跃,但在感染宿主细胞和复制时却会发生突变和进化。由此产生的对病毒遗传密码的调整可以帮助它更容易地在人类之间跳跃或逃避免疫系统的防御。SARS-CoV-2病毒的三种突变体促使专家加倍努力遏制冠状病毒的传播。
———————————————
第三部分:新冠病毒为什么会导致重复感染?
从根本来说,如果没有基因突变,就不存在任何生物。而对于冠状病毒来说,不断的进行基因突变所提升的免疫逃逸能力又有什么作用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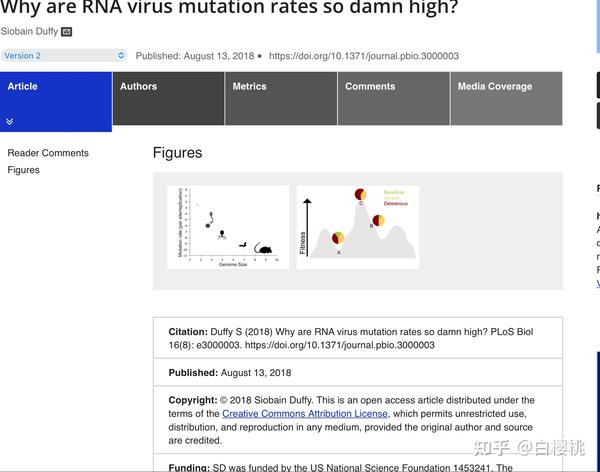
我们知道,新冠病毒是一种RNA病毒,他所有的遗传信息都只存在于一条RNA单链中。单链RNA在遗传复制的过程中比DNA更容易出现错误,因此在病毒不断复制的过程中,不断地产生变异/突变。
而冠状病毒的遗传代数越多,产生的错误越多,出现的变异就越多。而我们想知道的到底还要传播几次,就要看冠状病毒复制代数的时间快慢。
不过有一点要明确的是:RNA病毒的突变率很高——比宿主高一百万倍——这些高速率与毒性和进化性增强有关,这些特征被认为对病毒有益。冠状病毒的突变率几乎高得令人灾难性,突变率的微小幅增加可能导致RNA病毒灭绝。
突变是大多数进化的基石——它们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是我们在进化中看到的许多新奇事物的原因[1]。然而,大多数突变对拥有它们的生物体没有好处。许多突变导致生物体随着时间的推移留下的后代越来越少,因此自然选择对这些突变的作用是将它们从种群中清除出来。虽然一小部分突变是有帮助的,有些是无关紧要的(实际上是中性的或近中性的),但很大一部分突变是有害的[2]。虽然有害与有益的突变部分可能会在不同的生物体、不同的环境中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但有害突变的数量总是超过有益突变[2]。
这也从另一方面解释了尽管毒株不断变异,但是在致死率和传染性上是成反比。所以我们现在所谓的第一波传染高峰和第二波、甚至未来可能出现的第三波高峰,实际上对于毒株而言可能已经突变了数十数百次。
而病毒通过不断的传播迭代,复制过程中不断产生变异,这些突变积累到一定数量,会直接改变毒株本身的结构,而我们人体既往感染过或者接种过疫苗而产生的抗体,对于改变后的毒株的中和能力下降,就会导致无法完全/不能清除病毒,这也就导致了病毒的免疫逃逸——二次感染/复阳。
参考文献:
- 1.Baer CF. Does mutation rate depend on itself. PLoS Biol. 2008;6(2):e52. pmid:18303954
- View Article
- PubMed/NCBI
- Google Scholar
- 2.Loewe L, Hill WG. The populations of mutations: good, bad and indifferent.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2010;365(1544):1153–67.
- View Article
- Google Scholar

